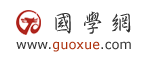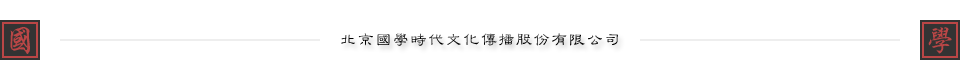奶粉注册实施一年 婴幼儿配方数量锐减
百度 马思纯和周冬雨 俩人的闺蜜情可以说好的让人羡慕了,私下的画风也是随便怼来怼去。二十余年前,我先后发表了《论宋代相权》[1]和《论宋代皇权》[2]两篇文章, 在质疑通说的基础上,初步提出了我的新皇权论。二十年来,对于皇权和相权的问题,间见论述。其中也包括对我的观点的质疑与批评。对此,不断有朋友希望我对这些批评做一些回应,可是我一直没有在国内的学术杂志上发表比较全面的意见。最近,又在网上看到了一篇被广泛转载的《宋代皇权与相权关系研究综述》[3],同以前看到的评论一样,将我列为其中一种观点的代表,才觉得有必要将我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做一些整理,以期澄清一下迄今为止对我的观点的误解,并报告一下我在80年代以后对皇权研究的进展。非常感谢这次宋史学会为我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在这里我想简单地整理一下我这二十年来的皇权研究,对其中主要的观点略加介绍,同时也介绍一下日本学界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这篇匆忙赶出来的文字,主要是我日文论著中部分片断的翻译,并不是一篇严格意义上的论文。诚请各位朋友,特别是年轻的朋友多加教正。
一、日本学界的皇权认识与我的研究回顾
人们似乎有这样的感觉,我在二十余年前的两篇文章之后,便已销声匿迹。因为在国内的学术杂志上再也没有见到我关于皇权问题的集中论述。而人们在回顾这一领域的研究时,只能像是品评化石一样来评论那两篇文章。其实,我在1990年远赴东瀛之后,一直厕身于日本的宋史学界,一直也没中断对于皇权以及中国政治史的研究。由于发表的论文多为日文,所以几乎不为国内的学界所知。为什么到了日本之后,我还执著于皇权研究呢?这并非是我有着强烈的学术坚持,而主要是基于日本学界对于皇权的认识。
长年在日本从事中国史研究,深感两国学界在深层次上的学术交流与沟通的不足。两国的学者都是立足于本国的学术成果之上展开研究,对于对方的研究成果所知甚少,更少利用。比如我在80年代前期写那两篇文章时,就完全不知道日本学界对于皇权的基本认识。这里面,固然有语言障碍和缺乏文本流通渠道的问题,但也有一个主观上缺乏必要性的认识问题。否则,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这是两国学者在研究上都存在的共同问题。
二十余年前,我写那两篇文章时,对于皇权和相权的通行说法,只能溯源到40年代的钱穆的《论宋代相权》[4]。其实,日本的中国史学界,以内藤湖南为代表,早在二十世纪20年代就已经提出了君主独裁制说[5]。在内藤湖南之后,从40年代的佐伯富[6],50年代的宫崎市定[7],70年代的周藤吉之[8],直到目前的梅原郁[9],都是坚持这一认识。过去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学界,分为京都学派和东京学派(历研派)。两派在很多领域很多问题上都存在分歧,但对皇权的认识上则没有分歧。从上述的研究谱系看,日本学界主张的君主独裁制说,与中国学界的通说君主专制论,在本质上并无二致。只不过日本的君主独裁制说主要是限定在宋代和宋代以后,而中国的君主专制论则从帝政创立直到终结,纵贯两千年间。因此,可以说君主专制论是一个超越国界的共同问题。有鉴于此,赴日之后,我觉得有必要将政治史中的皇权研究继续进行下去。从90年代后期开始,我陆续在日本发表了下述有关论著。
1.再论皇权——兼答富田孔明的批评(《东洋文化研究》创刊号,1999年)
2.“圣相”李沆——君臣关系个案研究之一(《中国社会与文化》第15号,2000年;中文版:《文史》第52期收录)
3.“平世之良相”王旦—— 君臣关系个案研究之二(《东洋文化研究》第2号,2000年;中文版:台湾大学历史学系编《转变与定型:宋代社会文化史学研讨会论文集》收录)
4.宋代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一个侧面——以范仲淹为中心(《东洋学报》第82卷第2期,2000年;中文版:河北大学《宋史研究论丛》2005年第6辑收录,题为:宋代士大夫主流精神论——以范仲淹为中心的考察)
5.再论皇权(之二)——从思想史视角的考察(《东洋文化研究》第3号,2001年)
6.以上述论文为基础,整理出版之专著:《宋代皇权与士大夫政治》(汲古书院,2001年)其中第八章,移译为中文,题为:《代王言者――以宋真宗朝翰林学士為中心的考察》(《漆侠先生纪念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
7.王安石新法——祖宗不足法(《中国》月刊 第13卷第1期,2002年)
8.徽宗与蔡京——权力的纠葛(《亚洲游学》月刊 特辑:徽宗及其时代,2004年)
9.通史著作:《中国史略》(DTP出版社 2006年)
如果把我的皇权研究分为两个阶段的话,那么,就是出国前为第一阶段,出国后为第二阶段。第二阶段研究可以说是对第一阶段研究的调整修正、补充和深化。由于第一阶段的两篇文章一反成说,在海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反响。日本的富田孔明在1995年的一篇论文中说我的文章全面否定和颠覆了迄今为止的君主独裁制说[10]。在各种反响中,有一种批评,说我过分强调了皇权和相权的对立。即作了这样的归纳:通说是皇权强、相权弱,王说是皇权弱、相权强。并批评我和旧说一样,在强调此强彼弱的对立这一点上,并没有摆脱一元论的框架。后来,这种批评成了对我的观点的定性。凡是评论我以前那两篇文章的人均如是说。从网上看到,国内和港台的历史教学,也这样介绍我的观点[11]。其实,这种批评与介绍,对我的观点存在部分误读。
由于需要服从论述的主题,自然在《论宋代相权》一文中,我主要强调的是相权,而在《论宋代皇权》一文中,则主要强调的是皇权,对彼此的关系也主要是着眼于双方对立的一面。但同时我在《论宋代皇权》一文中也说到:“一般说来,皇帝与群臣,特别是与宰执大臣,并不总是处于对立状态。相权增强,往往还同宰执与皇帝关系密切有一定的关系。”遗憾的是,持这种批评意见的人,几乎都没有注意到我的这种表述。不过,也不能说是批评者完全冤枉了我,误读了我。应当感谢的是,这种批评促使我对以往的研究进行了反省。之所以产生了不止是来自一个人的这种批评,还是说明我的论述存在着偏颇与不充分。反省和思考的结果,使我展开了第二阶段的研究。上述论著反映的就是我的第二阶段的研究。
简单地归纳说,我的第二阶段研究前提是,把皇帝看作是与官僚士大夫同处于一个政治体制中的一员,把皇权看作是同一权力结构中的一部分。君臣之间,不仅有着以往的研究所强调的互相制约的一面,更有着互相支持的一面。而这一面则是我在第二阶段研究的主要着眼点。同时我感到,对于皇权在政治体制内如何作用的问题,只是一般性的泛泛而论是难以解决的,而且这样论述也缺乏说服力。因此,我决定深入到政治活动的细部,来考察权力运作的具体状态。于是,我选择了宋代第一个正常即位的真宗,把以宰相为首的执政集团的活动作为考察对象,以期明了君臣协作下的宰辅专政的实际状态。以上的论著主要是围绕着贯穿于北宋第三代皇帝真宗在位26年间的五人宰相李沆、王旦、寇准、王钦若、丁谓的活动,加上起草皇帝诏命的翰林学士的作用,以期窥一斑而见全豹。
二、关于皇权、相权以及政治史的若干定义
尽管抽象论述缺乏说服力,但在这里并没有充分的时间与篇幅让我将具体的研究详细展示出来,只能将高度概括出来的若干概念介绍给诸位。
(一)皇权
从皇帝制度创立之日起,皇帝便被赋与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权力。然而,皇权究竟是皇帝个人所持有的权力,还是以皇帝为代表的政府的权力,即公权力,遗憾的是从来没有在制度上的明确界定。因而,就连皇帝本人也不十分清楚自己的权限,常常以个人的意志取代公权力,将二者混同。而历代的官僚士大夫,则基于“天子无私”的理念,努力将皇权限制在公权力的范围之内。当然,历代出于各种政治目的,主张无限放大皇权的,也不乏其人。由于皇权具有这样的界限不明确的特质,研究者在考察皇权时,也往往将二者混淆。过去,这个问题也像梦魇一样长期困扰着我,总是试图将二者理清,结果则是“剪不断,理还乱”,治丝益棼。到后来,才知道这种努力是徒劳的。正像中国传统政治的许多领域都存在有界限不明确的特征一样,皇权的这种不明确性,其实是一种出于有意或无意的政治设计。界限不明确,正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特征之一。比如公与私的区别,有时是谁也说不清楚的。就像元曲中描述的那个打碎了的泥人,“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12]。因此,对于皇权,只要做一个广义和狭义的界定就足够了,没有必要将二者勉强区分,实际上也区分不开。皇权的这种特质,正如同一个人具有两副面孔一样。西方学者在研究欧洲历史上的王权时,有“两个身体”之说。就是指的作为个人的王,同时是代表公权力的王。过去士大夫所说的“天子无私”,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限制皇权膨胀的理由。皇帝的权力与皇帝的地位是分不开的。但皇帝的公开的、甚至是包括不少私下的活动,都处于官僚士大夫的监督与规范之下。
关于皇帝的地位、权力及其作用,我想使用两个比喻。一个是帽子。帽子不仅仅是遮风挡雨的道具,往往还具有象征意义。特别是过去的乌纱帽,对于官员来说,尤为重要。有了它,就显示出官位与权威,失去它,则无异于被罢官。如果把过去中国的官僚政治体制比做一个人,那皇帝就是这个人头顶上戴的那顶乌纱帽。在君主制的政体之下,不能没有皇帝这顶帽子。再一个是公文与印章。以宰相为首的执政集团所主持的政治运营,就像一篇公文的实际内容,而皇帝在形式上的最后裁决,就如同公文所加盖的印章。光有印章,没有内容,公文就没有任何意义。反之,光有内容,没有印章,这个公文也缺乏效力。关于皇权与政治体制的关系,我觉得应当导入国体与政体这样的政治学概念来说明。即中央集权制度是显示国家统治权所在的国体,而君主制则是显示国家组织形式的政体。中央集权制度下的皇权,只不过是国家权力系统中的一部分[13]。
(二)宰辅专政
针对史学界的君主专制和君主独裁的通行提法,我提出了宰辅专政的概念。宰辅专政并不是指宰相个人的独断专权,而是指以宰相为首的执政集团在中央政治运营中的决策形态。宰辅在文字上指的是宰相与辅弼大臣。宋人使用这个词,用来指执政集团全体。我们先来看一下正史中有关的门类设置与词语表述。在《新唐书》中设置有《宰相世系表》,而在《宋史》中,与之相应的设置,却叫《宰辅表》。表名由“宰相”到“宰辅”的变化,不仅仅是反映了唐宋之间氏族观念的变化,还折射出政治结构的变化。《宋史》的《宰辅表》的题名与内容的变化,反映了宋朝国史的编纂者和元朝《宋史》修撰者这样两朝士大夫的认识。《宰辅表》的记事,不再限于宰相个人,而是以宰相为首的执政集团全体成员的任免状况的记录。从史书的变化上,也可以窥见从宋代开始,在士大夫政治的大背景之下,以宰相为首的执政们,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事实。这个位于士大夫政治高端的执政集团,在政治运作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我想这正是史书的记述产生变化的主要原因。
根据宋元人的认识与宋代的政治特征,我将我所论述的相权的外延加以扩展,指的并不完全是宰相的个人权力,而是以宰相为首的执政集团全体的权力。在宰辅专政的形态下,并不排斥皇帝的作用,皇帝也是同一统治体制中的一员。置于君主制政体之下的士大夫政治,官员的升降任免以及决策施策,尽管主要决定于以宰相为首的执政集团,或者是决定于各种政治势力间的角逐,但决不能说与皇帝完全无关。所有的决定都必须以皇帝的名义来表示。无论是执政集团也好,还是各种政治势力也罢,都不能无视皇帝的存在,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尊重皇帝的意志。从这个意义上说,宰辅专政实质上是在皇帝合作下的专政。在这样的政治形态之下,皇帝的合作最为重要。因而执政集团为了取得皇帝的密切合作,最大限度地吸收皇权,往往不是将意志强加于皇帝,而是软性对应,时而向皇帝做出一定的妥协,充分照顾到皇帝的面子。作为官僚个人,与皇帝关系的亲疏,同其官场沉浮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然而,从实际作用上看,在决策过程中,皇帝并不担当决定性角色。一般说来,与执政集团相结合的皇权,才是强有力的皇权,反之则是孤立和无力的。同样,有了皇权的支持,宰辅专政才得以实现。二者之间是互补关系。
(三)士大夫政治
士大夫政治是指以士大夫为主体的官僚政治。我的考察基点之所以定在宋代,不仅仅是因为对这一时代的史料比较熟悉,更主要是,宋代是一个承前启后,极有特色的时代。关于宋代的时代特征,业已有许多学者论述。我以为最大的政治特征,就是士大夫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或者说势力获得了空前的成长。这个时代被日本学者认为是中国的近世或者是前近代开始的时代[14]。从这个时代开始,通过科举进入政界的士大夫,支配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主流政治。为了把这种政治形态与欧美所说的文官政治相区别,并且凸现其时代特征,我称之为士大夫政治。
这种知识人占绝对支配地位的政治形态,让表面上依然是君主独裁的政治制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政治舞台上,皇帝不再担当主角,而是成了配角。皇帝或许可以罢免作为个人的官员,却无力与士大夫阶层全体相对抗。实际上,皇帝如果不与朝廷的某种政治势力联手,几乎不可能轻易地罢免宰相或是执政大臣。因此,皇帝必须采取合作的态度,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从这个时代起,皇权真正开始走向象征化。
在士大夫政治这样新的国家体制下,皇帝是一种特殊的存在,皇权也是一种特殊的权力。这是延续了千年的君主制政体所决定的。以士大夫为主体的政治形态,并非为宋代所独有,是从宋代开始,并为后世所承续的政治形态。作为历史长河中的一段流程,宋代不是孤立的时代,无论是皇帝制度,还是科举制度,都是从前代继承而来的。包括皇权观在内的士大夫的思想也是接受了前人,并影响了后世的。因此,可以说对宋代皇权的考察,具有通史性的意义。
(四)宗派政治
宗派政治(Factional Politics)是位于士大夫政治之下的概念。士大夫阶层相对于其他阶层,相对于皇帝,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或者说是一体性。在与外界发生冲突时,士大夫之间以往的恩怨往往会烟消云散,共同守卫全阶层的利益。然而,士大夫阶层和其他阶层一样,人的集结总会产生派别之争。在士大夫阶层内部,由科举而生成恩师、门生、同年等关系,由荐举和共事而生成故吏、僚属等关系,由婚姻而生成联姻关系,由志趣而生成友朋关系,由政治立场而生成党派关系,总之存在着大大小小的有形或无形的圈子和宗派。在传统中国的政治生活之中,党同伐异的派系角逐随处可见。在士大夫政治之下,所谓的皇权和相权之争已经成为次要的问题,政治斗争大多是以宗派之争的形态呈现的。这也是宋代党争异常激烈的原因之一。
在宗派政治之下,无论是作为言官的谏官御史,还是作为载笔者的侍从学士,无论是执政大臣,还是皇帝,都无一例外地成了宗派斗争这个大棋盘中的作用各异的棋子。在众多的棋子中,在宋代被称之为台谏的御史台官与谏院官是最具有攻击力量的,犹如象棋中的炮。本来在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中,按照原本的设计,言官的确应当是独立于皇权和相权之外的第三势力,但由于宗派政治的缘故,言官则事实上无法独立,不可能超脱于政治斗争的圈子之外。在政治斗争尚未激化之时,言官或许还可以行使其规谏君主“佚豫失德”[15]和“绳纠执政之不法”[16],但当政治斗争趋于激化之时,言官几乎毫无例外地成为某一政治势力的鹰犬[17]。
走向象征化的皇权,尽管有着空洞化形式化的一面,但由于直至最后也没有完成象征化的缘故,毕竟还有着实体性的一面。所以在君主制政体中的党争背景下,皇帝像神佛一样被尊崇着,皇权作为战胜对手的王牌,成为各方争取的对象。只要能与皇帝结盟,左右皇帝,就可以在党争中掌握主导权。位于政界顶端的以宰相为首的执政集团,是宗派政治中的执政党。但执政党也常常会产生分裂。在党争中,皇帝没有超然置身于局外的可能。并且,卷入党争旋涡的皇帝并不能主导党争,只会被党争左右,成为某一派系的利用工具。宋代的政治运作,并不是君主独裁,而是以宰相为首的执政集团的专政。即前面说的宰辅专政。但宰辅专政也具有宗派政治的特征。人事任免,政策制定,往往可以看到宗派的影子。政治的正常运作时期,宗派活动潜藏于水面之下。党争激烈的非正常时期,则泾渭分明,势同水火。宗派政治不仅是士大夫政治的最主要的特征之一,也是中国的传统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如果从宗派政治的角度考察包括皇权在内的许多政治现象,几乎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我以为从宗派政治的角度入手,是研究中国政治史的一个关键。
(五)政治力学
这里并不是想机械地套用物理学的概念,而是取其相似性,借以说明政治活动的某些特征。
1.合力说。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权力也是一种力。从表面上看,多数的决策与人事任免,是出于皇帝或权臣的意志,但置于宗派政治的背景之下观察,实际上并不是如此简单。透过表面现象,几乎朝廷所有的重大举措,都是君臣间公开商议或暗自策划的结果,即各种力的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不是某一方面单独的力。这一点与物理学上说的合力很相似。当然力与力之间,并不是简单地相加,而是充满了较量和妥协。这里面则反映出各种力的利益诉求。较量和妥协的结果,则最终由某一种力占了上风,于是结果形成,达成平衡。
2.惯性法则。持有古代崇拜倾向的中国人,较之法律更重视先人或自己的经历和经验。这种经历和经验,在过去被称之为故事,在宋代,大凡本朝以前实施过的也叫做祖宗法。实际上,故事也好,祖宗法也好,都是一种惯例。政治的运作几乎就是由这样的惯例推动着。任何时代,任何地域,惯例一旦形成,就像行驶中的车子一样,很难停止下来。要想停止,除非强制刹车。然而在通常情况下,一般不会这样做,也没有必要这样做,而是任车子一如既往地运转。随着运转速度的增大,加速度也不断增加。许多宋代的所谓的祖宗法,实际上最初就是由某个人因某件事所形成的先例,从而成为了惯例。然而,人们往往在自己制造的惯例面前呈现出无力感。这与地位无关,皇帝也好,大臣也好,都难以抗拒惯例。在多数情况下,只能顺从惯例。还是用车子的比喻。改革之所以困难,就是难在试图让行驶中的车子停止下来或改变方向。这不仅是物理学的惯性法则的问题,还有一个现实惯性和人们的心理惯性的问题。人总是对未知和生疏的事物表现出本能的排斥,而对熟悉的东西感到亲切,并自然地接受。这就是加速度增大的原因。从而惯例形成的愈久就愈难改变。正所谓积习难改,或者说积重难返。正因为如此,人们较之法律,更重视惯例,而法律亦因惯例而生。这在重视祖宗法的宋代尤其如此。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有关宋代的编纂“类编故事”或“条法事类”的记载。当然,同样一个惯例,其效应具有着正面与负面的两面性。在政治上,不同的利益集团,站在不同的立场,总是制造于己有利的先例,并对既有的惯例,向着于己有利的方向加以微调。像这样政府以皇帝的名义实施的先例,对后来的皇帝来说,是一种制度上的制约。皇帝如果无视这些故事,无异于无视祖宗法,会要面临非难的压力的。从这个意义上,故事或祖宗法, 可以说是士大夫制约皇权的工具之一。
三、有关皇权的几个图示
(一)皇权结构模式
历来在说明皇权结构模式和描述体现君臣关系的官僚体制时,大多使用金字塔式的建筑物来比喻。在正四角锥型的金字塔结构中,皇帝位于顶端,皇权也位于王朝权力体制的顶端。人们对于这样的比喻很乐于接受,并不觉得有何不妥之处。因为制度的规定就是如此。无论是秦汉时代的三公九卿制,还是隋唐的三省六部制,当对其结构加以图示时,皇帝自然要放在最上部。然而,我觉得金字塔式的比喻还是有些问题的。因为如果是金字塔式的结构,那么位于顶端的皇帝,来自下面群臣的,只有支持,而无任何制约。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考察实际状况,我觉得似乎用拱桥形来描述皇权结构和君臣关系更为贴切。拱桥形是半圆弧形结构,多用于门窗桥梁的上部。在拱桥形上部的砖石中,位于最中央顶部的砖石可以看作是皇帝或皇权,两侧的砖石可以看作是群臣或政府权力机构。中央的砖石受到来自两侧砖石的挤压。这种挤压,既是支持,又是限制,使之不得随意活动。而中央的砖石对两侧的砖石也是一种支持和限制。砖石与砖石之间,构成了一个统一体,谁都离不开,缺一不可。一旦脱离,整个结构就会崩溃瓦解。


图1:金字塔形示意图 拱桥形示意图
(二)权力与权威的关系
现代政治学理论一向把权力(power)和权威(authorityfa)区分开来,而不是等同视之。
1.权力递减的观察。力在作用过程中,如果不追加能量,就会逐渐衰减。犹如一颗石子投入水中,最初的波纹最深,随着向四方扩散,波纹逐渐便浅,直至消失。皇权的行使,最初或许是出于皇帝本人的意志,但与执政集团或者其他强势势力的意志发生抵触时,在传达和执行的过程中,下述的情形则很有可能发生。首先是起草敕令制诏的知制诰或翰林学士之类的文臣,将自己的私货加入,然后是宰相和执政大臣以自己的意志加以变更,到了最后,以皇帝名义发布的政令,就几乎与皇帝的初衷毫不相干了。反过来看,政令所反映的则是朝廷中强势集团的意志。被歪曲的皇权也是皇权,但并不代表皇帝本人的意志。以上是从政令的具体发布过程来看的。如果从皇权的整个走势来看,在皇权走向象征化的过程中,皇帝实际行使的权力逐渐被政府权力所吸收和取代。从这个意义上看,也是一种权力递减。
2.权威增大的观察。皇权实际上主要反映的是皇帝的权威。在皇帝的地位逐渐走向象征化的背景下,皇帝个人所握有的实际行政权力越来越缩小,皇帝的权威却越来越增大。关于这一点,我想具体用图形来说明。当一个王朝创立之初,或是皇帝可以充分行使行政长官的职能时,其权力与权威是合一的。用圆来表示,权力与权威处于同心圆的圆心一点上。但当皇帝逐渐从行政长官的角色中淡出,政府首脑的作用则日益凸现,这个时候的同心圆就被拉成了椭圆。因此权力和权威发生分离,形成了两个圆心。权力成为政府的权力,权威则是皇帝的权威,二者同处于一个椭圆,即同一统治体系。权威辐射涵盖整个椭圆,烘托支持权力,权力则利用和体现权威。


图2:权力与权威转化示意图
(三)皇权走向的两个“至高无上”
中国历史上的皇权走向,如果用坐标来表示的话,似乎应当是下图的情形。随着历史的发展,实质性的皇权逐渐下降,反过来象征性的皇权逐渐上升。就是说,皇权经历了由实质性的至高无上向象征性的至高无上的变迁。这种变迁也可以说是从权威的权力向权力的权威的变迁。在这个图中,我用纵坐标表示皇权的升降,用横坐标表示历史的发展。横坐标的每一区间从左到右表示一个王朝的开始和终结。坐标轴以外的实线表示实质性的皇权的变迁,虚线则表示象征性的皇权的变迁。

图3:皇权变迁坐标图
用图形来示意,总有将复杂的历史线形化、简单化之嫌。并且,正像任何比喻都不能等同比喻本体一样,任何图表也不可能做到完全贴切。但图表的好处就在于一目了然。这个图仅仅是意在描述皇权变迁的基本趋势。自不待言,历史的发展呈曲线形,实际的状态复杂而多样。
四、皇权走向象征化的历史因素
通过对中国传统政治的考察,我们可以寻绎到皇权从实体化走向象征化的轨迹。
考察这个问题时,首先应当把视线投向皇位世袭制。从这个角度考察,可以形成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开国君主大多是通过战争、政变等非常手段夺取政权的。这种取得政权的方式,势必使开国皇帝大权在握,成为行政首脑,而绝不可能成为仅具象征意义的礼仪性的虚位君主。然而,由于人的生理极限,即使是极有能力和精力的皇帝,也不可能做到事必躬亲。这就给以宰相为首的执政集团的权力发展留下了空间。
第二,能够取代前政权而登上皇位的开国皇帝,一般说来具有较强的能力,非属平庸之辈。而后继的君主,则往往与自身的能力无关。即位登基,一般也不需要经过激烈的角逐,仅仅由于宗法关系而继承了皇位。即位的君主缺乏政治实践与政治经验,更缺乏政治威信。这种皇位世袭制,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人主的低能。仅此一点,后继君主就势必要比开国皇帝显出弱势。他所拥有的名义上属于他的权力,往往并不代表他的政治实力,而仅仅由皇位这一特殊地位所带来的。因而这种地位更多的是带有一种象征性。
第三,在皇位世袭制下即位的皇帝多是幼主。由于尚未成年,难以理政,所以决事多由前朝顾命元老和宰执大臣。新君对于前朝元老,往往是毕恭毕敬,唯恐不尊。这就使新君从即位之始,便直不起腰身,受宰执所左右。例如宋真宗即位时,虽已非年幼,但史载,“(真宗)对辅臣于禁中,每见吕端等,必肃然拱揖,不以名呼。端等再拜而请。上曰,公等顾命元老,朕安敢比先帝”[18]。若是幼主,就更离不开顾命大臣的辅佐。从辅佐到亲政,不仅不起实际作用,也大多养成了事事听命于大臣的庸懦性格。因而,君弱臣强亦势所必然。明代的皇帝,除了洪武和永乐,也多以“先生”称呼实际的宰相内阁大学士,尊为师长。历史上频发的外戚、宦官、权臣弄权与太后摄政,都是假皇权之威来行弄权之实。这一方面反映了皇权的变质,另一方面也正显示出皇权的巨大象征意义。
第四,除了开国皇帝,后世的皇帝自幼就在保傅制度下接受严格的君道教育,即位后,又有侍读侍讲制度进行继续教育,这使多数君主都具有一定的自律性,能在士大夫规定的“雷池”中循规蹈矩。较之规劝皇帝过失的谏官制度,保傅制度和侍读侍讲制度是一种防患于未然的更有效的预防机制。用朱熹的话说,是“谏心”之制[19]。这种“谏心”之制必然使皇帝主动向以宰相为首的执政集团让权。其结果是皇权逐渐虚化。
以上所述,大多并非中国史上的皇帝制度所独有,几乎是世界史上王位世袭制下的君主执政的共性问题。尽管如此,依然可以看作是皇权走向象征化的一个因素。
如果说皇位世袭制是导致皇权走向象征化的皇帝自身因素,那么政治制度的逐渐完备则是导致皇权象征化的主要的并且是决定性的因素。这是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从中国历史的整个历程看,有一个政治制度逐渐走向完备的过程。二是从各个王朝看, 政治制度也有一个逐渐走向完备的过程。
我们先从中国历史的整个历程来观察。
秦始皇时期,随着皇帝制度的创立,形成了至高无上的皇权,但那个时期却尚未形成完备的政权体制。因此,这个时期君主作为行政长官的职能显得特别突出。而宰相等大臣则基本处于日常事务的处理者和政策的执行者的地位。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政权体制日臻完备和政治运作渐次成熟,政务分工亦愈加细密而具体,宰相或以宰相为首的执政集团的决策功能也愈加强化。因此,君主直接参与处理政事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少。皇帝除了其象征意义之外,在整个政府机器的运转中,成了“多余的人”,其主要作用是“图章”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成熟的政权体制本身,就是对皇权的一种排斥。南宋末年的一个监察御史就说: “政事由中书则治,不由中书则乱。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20]这表明,在完备的政治体制之下,皇权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几乎没有立足之地。到了明代,不少君主几年,甚至几十年都不迈出宫门一步,政事基本上全由实际上的宰相内阁大学士来处理。清人郭嵩焘就说,“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21],可谓是一语中的。
我们再从各个王朝的发展来看。
开国皇帝或准开国皇帝(如宋太宗与明成祖以及经过激烈角逐而登基的清朝诸帝等)对政府的行政事务有着较多的干预。但当政权运作走上正轨,政权体制和各种制度逐渐完备之后,就像计算机执行程序一样,几乎所有的政务都按照既定的法规由惯性来推动。在王朝的草创期结束后即位的皇帝,对政府行政事务的关心程度和影响力都逐渐开始减弱。正相反,与此同时,以宰相为首的执政集团则自然占有了这个权力空间,成为政治运营的主要角色。因此从这一时期开始,皇帝必然与开国皇帝不同,基本上从行政长官的角色退役,成为不需要事必躬亲的名义上的君主。
从开国皇帝到后继皇帝,皇权渐渐产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这种变化,用近代以后的共和政治体制来形容的话,就是由总统制转向了以总理为负责人的议院内阁制。在总统制下,总统既是国家的礼仪性的元首,也是最高的行政首脑,对一切行政事务负有责任。然而,在议院内阁制下,总统仅仅是礼仪性的国家元首, 对一切行政事务不再负有责任。
总之,考察传统中国的皇权,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君主为了形成强大的皇权,而建立起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然而,为这一制度的创立者所始料不及的是,历史的发展,竟使这种集权制度成为皇权的“克星”。皇帝及其谋臣共同创立的巨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机器一旦开动,上下一致都跟着运转。无论是皇帝,抑或是大臣,谁都不可能完全成为这架机器的操纵者,都不过是这架巨大的机器上作用各异的互相合作互相制约的齿轮和螺丝钉。皇权也成为国家权力的一部分。
制度的完备需要制度外的保障。这种保障,是一种皇权之外的政治力。尽管历代都有这种政治力,但历史发展到了宋代,空前崛起的士大夫阶层,从上到下形成了对政治的全方位的支配。由这种支配所生成的责任感又培育了空前活跃的士论。依存于士大夫政治的士论,或者称之公议,是防止皇权以及其他权力从制度的框架中脱逸的最有力的制约。这种制约让皇权以及所有权力必须遵从士大夫政治所既定的轨道。皇帝以及所有的权力持有者都无法同这种政治力相对抗。除了传统的天道、道理和法规之外,在宋代,祖宗法和公议是限制皇权和其他权力暴走的两大利器。如果说祖宗法还属于制度性的限制的话,公议则是舆论的限制。对于祖宗法,有时还可以公开声称“祖宗不足法”,但很少有人公然藐视公议。政治体制的成熟,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呈渐进性。因而,从总的历史趋势看,皇权从实体性走向象征化,是和政权体制的成熟同步渐进演化的。
考察传统中国的皇权走向,从断面的历史看,在每一个朝代,伴随着从王朝创立到王朝衰微,实体性的皇权都经历了一个由盛到衰的的过程。而每一部分断面的历史,都是纵向发展的历史的一部分,反映的都是皇权演变的某一阶段与过程。如上述图示,从整个历史的发展趋势看,实体性的皇权由高向低渐性发展。反之,象征性的皇权则由低向高渐性发展。传统中国的皇权,从实体性到象征化,经历了两个至高无上的演变。
那么,怎样评价皇权走向象征化的趋势呢?从客观意义上说,这一趋势反映了政治的进化,国家管理由家长式的原始形态,走向制度化、科学化。从道德意义上说,这一趋势反映了从专制走向民主的过程。除此之外,绝对的君主专制在传统中国被抑制的事实,似乎可以部分地回答史学界曾经长期争论的难题,即中国封建社会为何长期停滞的问题[22]。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想到了英国阿克顿的那句经典名言,即“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23]。 所谓绝对的权力是指高度集中的、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的权力。从历史事实看,君主不可能做到完全独裁,因而就不拥有绝对的权力。而由于传统中国的互相制约的政治设计,其他任何势力也难以长期拥有绝对权力。在传统中国中,由于绝对权力的不存在,所以很难导致绝对腐败的发生。即使产生局部的一时的问题,贵族政治或是士大夫官僚政治的自身机制可以进行调整,不断给予王朝的母体灌注活力。我认为这正是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延续的一个原因。
五、中国为什么没有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
我讨论的皇权,主要并不是着眼于皇权与其它权力的对立,而是注重于皇权的象征化的演变。并且我的皇权思考并不局限于宋代,是一种通史性的通盘思考。了解了我的上述见解,也许有人会问,既然说传统中国的皇权逐渐由实体性走向了象征化,那么,为什么中国没有形成迄今依然存在于东西方一些国家的君主立宪制政体呢?对此,我想列举出如下因素来试加回答。
第一,中国历史上频繁的政权转换、王朝更迭,使中国的皇帝难以最终走向神的境界,虽说是神圣,也被称为天子,但是毕竟“人固可为[24]”的人间世俗帝王。仅此一点,就使皇权难以彻底完成象征化。
第二, 在新王朝建立之初或是在特殊的政治背景之下,皇帝曾经作为政府首脑,位于政务处理的前台。因此皇帝必须为自己的政治过失,甚至是政府的政治过失负责任。历史上屡见不鲜的皇帝罪己、禅让,正是受行政长官的名分所累。由于有过这样的经历,并且从未彻底地退出过政治舞台,加之也不情愿退出,所以,皇帝就不能完全被神化,也就不能彻底走向象征化。
第三,历史上经常性的改朝换代,使原本再一个王朝内业已走向象征化的皇权,在新王朝建立之初又得以“返祖”,回归为实体化。尽管政治体制随着历史的进化愈加完备,但历史过程的反复,妨碍了皇权最终走向象征化。
第四,中国君主制的最后一个王朝是清朝,是由满族人入主中原的政权。尽管在中原经历了数百年的民族融合,但仍有着民族排斥的问题,尤其是清末的革命运动又夸大和煽动了民族对立的历史与现实。因此,进入近代以后,爆发了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号召的辛亥革命。加之西方共和政治的影响,使得辛亥革命在推翻清朝的同时,连同君主制也一起埋葬掉了。
第五,偶然性决定了历史。我一直认为,中国社会如果顺其自然地发展,步入近代,当是君主立宪制政体。中国历史已经走到了这个边缘。尽管历史不允许假设,但我仍想大胆做个假想,如果当年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戊戌变法”成功,今天的中国或许跟日本一样,是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亦未可知,只是阴错阳差,历史走进了另一个胡同。我的这个想法,在1985年的时点,不方便在文章中直言,但已经在文章的结尾做了暗示,并且在1989年的文章中,再次引用了这个暗示[25]。
六、关于研究方法的余论
为什么我的研究会得出与历来的研究几乎完全相反的结论?我以为似乎主要应当归结为方法问题。
人们在形容看问题有片面性时,经常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我想将这句话套用过来。长期以来,在中国史研究领域,往往是“只见制度不见人”,即只是停留在对制度的不惮其烦的考证上。在考察制度的沿革时,也是从制度到制度,却忽视或者说起码是轻视了一个最重要的因素。这就是在制度运作过程中人的活动。相对而言,制度是死的,是静态的,人是活的,是动态的。任何制度都要靠人来运作。人的活动在制度的运作中至关重要。因为制度本身与制度的实施不尽一样,甚或是大相径庭,完全相反。这种现象,古往今来,概莫能外。就是说,制度本身是个常数,而制度的具体实施则是一个变数,甚至是充满了变数。王安石变法实施青苗法的过程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而制度的变迁,则正是由于人的活动与制度运作时的调整与改变。我的研究的着眼点,重在制度实际运作下的人的活动。我在二十年前那篇《论宋代相权》的开头便指出:
要区别开这样两方面的问题:第一,君主的主观意图与政治舞台上的客观事实;第二,制度的设立与制度的实施。比较这两方面问题的两极,前者自然不应忽视,但后者则是更重要的方面,是决定问题性质的方面。历史的发展,政局的演变,是有其内在的原因的,而不是以某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政治舞台上风云变幻的事实与制度的具体实施,往往与君主的主观意图及制度设立之初衷相悖。因此,如果我们只注意了前者,忽视了后者,就往往会惑于一些表面现象,难以揭示出潜藏于表象之下的本质性的东西。
我这样的强调人的活动,并不是不重视对制度本身的研究。作为基础性的研究,制度的研究不可或缺。只是不能 “只见制度不见人”。与我所说的制度的设立与制度的实施相映成趣的是,最近读到的马克斯·韦伯的一段话:
政治行为的最终结果,往往不如人愿,与当初的意图相违,甚至常常相反。这种情形是百分之百的真实,是一切历史的基本事实。[26]
这里,韦伯强调的也是实际政治运作的结果。
对于制度史研究所存在的偏向,已经逐渐为研究者所认识。在2000年, 当时的韩国东洋史学会会长李成珪在东京演讲时说:“我有两个忧虑,一个是对较之动态的发展过于强调静态的循环感到忧虑,一个是对忽视宏观的历史体系的理解,停留微观的分解上感到忧虑”。而邓小南先生的“走向活的制度史”[27]的呼唤,则引发了更为广泛的共鸣,令人欣喜。
注释:
[1]《论宋代相权》,载《历史研究》1985年第2期。
[2]《论宋代皇权》,载《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
[3] 桂始馨《宋代皇权与相权关系研究综述》
[4] 钱穆《论宋代相权》,《中国文化研究汇刊》1942年第2期。
[5] 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载《历史与地理》1922年第9卷第5号。
[6] 佐伯富《王安石》,富山房1941年出版。
[7] 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教育时报社1950年出版。
[8] 周藤吉之、中岛敏编著《中国的历史》5,讲谈社1974年出版。
[9] 梅原郁《宋代官僚制度研究》,同朋舍1985年出版;《皇帝政治与中国》,白帝社2003年出版。
[10] 富田孔明:《宋代君主独裁制说再检讨》(《小山义久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集》,1995年)。
[11] 对此,可以例举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网页(两宋制度史专题:http://history.m327.com/dispbbs.asp?boardID=2&ID=31&page=3)与香港的教学纲要(1, 中國歷史科工作紙 2,中史教室)。
[12] 《历代诗余》卷119(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
[13] 虽然不是主流认识,但值得注意的是,与我的观点在实质上接近的日本学者的提法有“皇帝机关说”。这一说法无疑是受到30年代在日本引起极大政治争议的“天皇机关说”的启示。这种说法,主要是把皇帝与国家视作一体,强调皇帝公共形象的一面。此说主要见于寺地遵《南宋政权确立过程研究笔记》(《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第42卷特辑,1982年)和小林义广《欧阳修及其生涯和宗族》(创文社,2000年)。
[14] 一般说来,京都的学者通常使用“近世”,东京的学者则多用“前近代”。
[15]《徂徕文集》卷13《上孔中丞书》(《宋集珍本叢刊》影印本,线装书局,2006年)。
[16]《长编》卷360,元丰八年十月丙子条(中华书局,2004年)。
[17] 关于言官成为某一政治势力的鹰犬,而皇权几乎不能有效地支配言官这方面的史料,多得不胜枚举,可参见我的《论宋代相权》和《论宋代相权》的有关章节。
[18]《宋宰辅编年录》卷3咸平三年十月戊子吕端罢相条(《宋宰辅编年录校补》本,中华书局,1986年)。
[19]《群书考索》别集卷18《人臣门》(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2年)。
[20]《宋史》卷405《刘黻传》(中华书局,1986年新1版)。
[21]《清稗类抄》,中华书局标点本5250页。
[22] 我在90年代以后的文章,一直回避使用“封建社会”一词,而改称为传统社会或传统中国。在日本,包括封建社会在内的五种社会形态,被称为“世界史基本法则”,曾经支配了战后的日本史学界。从70年代起,日本学者开始逐渐挣脱这个藩篱,现在基本已无人使用。
[23]《自由与权力——阿克顿勋爵论说文集》(侯健、范亚峰译,冯克利校,商务印书馆,2001年)。有人指出,根据原文,“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应当译为“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这也许是正确的,因为在日文中就是这样译的。但现在的译文已为广泛接受,似不必更改,况且后一个“绝对”就是“完全”或“彻底”之意。
[24] 邓牧(1247—1306)《伯牙琴·君道篇》(中华书局1959年点校本):“彼谓君者,非有四目两喙,麟头而羽臂也,状貌咸与人同,则夫人故可为也。”
[25]《论宋代相权》的结尾写道∶“没有皇权的象征化和作为集体领导的相权的强化,恐怕也不会有迄今仍存东西方一些国家中的君主立宪制政体。”
[26]《作为职业的政治》,日文版,岩波书店,1980年出版。
[27] 邓小南:《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的点滴思考》(《浙江学刊》2003年第3期)。
(此文为2006年8月上海召开的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二届年会提交论文,收录于2008年7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宋史研究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