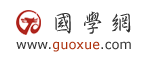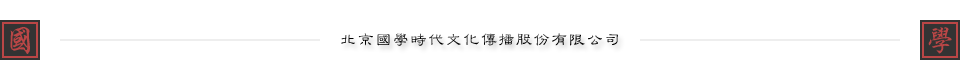驾驶证扣6分有什么影响
百度 李盛霖委员指出,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防范金融风险,重视地方债务,特别是隐性债务的化解,提出了明确要求,做了具体部署,建议国务院有关部门结合审计问题整改工作进一步采取措施,切实使化解地方债务特别是隐性债务风险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内容提要:钱穆先生是20世纪中国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大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他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名作。钱穆主要是从宋学的角度来研究清代学术,提出了清代汉学渊源于宋学,“不知宋学,则无以评汉宋之是非”的著名论断。由于钱穆治清代学术史主要以昂扬宋学精神为主旨,所以他在评价和判识清代学人学术思想的高下深浅时,就贯穿了一条是否有志经世、是否心系天下安危的宋学精神为其评判标准的。
关键词:清代学术史;钱穆;宋学;汉学
一
近人研究清代学术史较早者,首推章太炎先生。章氏撰有《清儒》一篇,对清代学术的发展变迁作了提要钩玄式的概括,可谓是近代总结清代学术史的开山之作。稍后的刘师培著《南北考证学不同论》、《近儒学术统系论》、《清儒得失论》、《近代汉学变迁论》,对清代学术作了富有价值的总结。继章、刘之后对清代学术史研究最有成就者,当推梁启超先生。1904年,梁氏在《新民丛报》发表《近世之学术》一文,这是他治清代学术史的发轫。不过这时的梁启超对清代学术的评价总体不高,认为“有清一代之学术,大抵述而不作,学而不思,故可谓之为思想最衰时代”。 这与他后来在《清代学术概论》“自序二”中,把清代考据学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并称为我国五大学术思潮的评价截然不同。梁启超晚年从政坛上退隐下来,致力于清代学术史研究,1920年写成的《清代学术概论》, 1923年至1925年间完成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他治清代学术史最负盛名的两部力作,集中体现了他在这一学术领域的研究水平。
继梁启超之后对清代学术史研究最有贡献的一位学者是钱穆先生。1928年3月,在苏州中学任教的钱穆在《苏中校刊》上发表《述清初诸儒之学》一文,这是他治清代学术史的开端。在1928年春完成、1931年出版的《国学概论》第九章“清代考证学”中,他对清代学术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如不能以经学考据来概括整个清代学术史,清代汉学开山应以顾、黄二人并举,并非顾炎武一人之力,吴学、皖学不同的治学风格和学术联系等,这些见解后来被采入了他的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当然,在钱穆先生跨入清代学术史研究的大门时,无疑受过他的前辈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等人的影响。在他的早年著作《国学概论》中,他引用过章太炎的《清儒》、刘师培的《南北考证学不同论》,多次征引过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的观点以证其说。尽管后来钱穆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写作主旨、研究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与梁启超大异其趣,然而以同样的题目来研究同一时空的学术进程,这本身就是对梁启超划定的这一学术研究领域的认同。
1930年,由于古史辨派的主将顾颉刚的识拔和力荐,钱穆由中学教师步入大学讲台,进入燕京大学任教。第二年,转入北大史学系。在北大任教时,除主讲中国上古史、秦汉史等必修课外,他还给学生开了一门选修课,那就是梁启超在天津南开大学和北平清华研究院开过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根据钱穆晚年的回忆,他最早接触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在1924年的《东方杂志》上。梁著“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四章,1924年在《东方杂志》上刊出过,钱穆首先在该杂志上拜读了梁著的这一部分内容。梁著全书出版后,他曾在北平东安市场某一书肆购得了这部治清代学术史的名著。梁氏此书以清代汉学为宋学的全面反动为基调来疏理清代学术史,多著眼于清代汉学与宋明理学的对立处。钱穆不赞同这一观点,所以他在北大史学系特开此课程,以阐发自己对清代学术史的见解。由于此课程是在梁启超卒后不久续开,所以备受学术界的注目。当时钱穆一面授课,一面编写讲义,前后五载,终于完成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部不朽的名著。钱著共分14章,上起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等晚明诸遗老,下至晚清龚自珍、曾国藩、康有为,共叙述了51位学术人物的思想。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抗战军兴,钱穆流转西南。1941年,在成都齐鲁国学研究所担任教职的钱穆接受重庆中央国立编译馆之托,负责编写《清儒学案》一书。在此之前,虽有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但江书仅迄乾嘉,又固守汉学壁垒,详汉略宋,殊嫌不备。继起者唐鉴的《清学案小识》,专重宋学义理,排斥汉学,分类牵强,其书止于道光季年,亦未穷尽有清一代学术原委。近人徐世昌所辑《清儒学案》208卷,1169人,止于清末,最为详备。然该书旨在搜罗,未见别择,被后世讥为“庞杂无类”。钱穆承担《清儒学案》的编写后,先读清人诸家文集,每读一集,始撰一稿,绝不随便钞摘。他托友人代为收购清代关学遗书二十种左右,有清一代关学材料,“网罗略尽”。勤读李二曲集,采其言行撰一新年谱,所花精力尤多。又遍览四川省立图书馆所藏江西宁都七子之书,“于程山独多会悟”。对于苏州汪大绅以下,彭尺木、罗台山各家集,也提要钩玄,“颇费苦思”。钱穆称《学案》一书的编写,以这几篇最有价值。全书约四、五十万字,共编孙夏峰、黄黎洲等64个学案,一代学林中人,大多网罗其中。著名历史学家柳诒徵先生在《审察<清儒学案>报告书》中称赞钱著“体裁宏峻,抉择精严,允为名著。” 该书字字皆亲手抄写。由于当时处抗战中,生活清苦,没有再找人另抄副本,直接将手稿寄到重庆中央国立编译馆。抗战胜利时,此稿尚未付印,全稿装箱,由编译馆雇江轮载返南京。不料箱置船头,坠落江中,葬身鱼腹。全书仅存序目一篇,在寄稿前录存,刊于四川省立图书馆主办的《图书集刊》第三期上。
陈祖武先生对近人治清代学术史作了这样一个简明而中肯的总结:“近人治清代学术史,章太炎、梁任公、钱宾四三位大师,先后相继,鼎足而成。太炎先生辟除榛莽,开风气之先声,首倡之功,最可纪念。任公先生大刀阔斧,建树尤多,所获已掩前哲而上。宾四先生深入底蕴,精进不已,独以深邃见识而得真髓。学如积薪,后来居上。以此而论章、梁、钱三位大师之清代学术史研究,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总其成者无疑当属钱宾四先生。……今日治清代学术史者,无章、梁二先生之论著引路不可,不跟随钱宾四先生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深入开拓尤不可。” 确为不易之论。
二
对于清代汉学的学术渊源及其与宋学的关系,近代学术界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清代汉学是对宋明理学的全面反动。此说以梁启超等人为代表。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就提出了“清学之出发点,在对于宋明理学一大反动”的主张,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他又详加阐述。在梁启超看来,十七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学术思想走上了一条与宋明学术完全不同的路径。这条路径一方面表现为一种反理学思潮(反对理学家空谈心性,束书不观),另一方面则发展为重实证的考据学。所以,他认为从明末到清季这三百年学术史的主潮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据此,梁著把对宋明理学的反动视为清代汉学的本质,并把汉、宋对立这一思想贯穿全书 。
钱穆不赞同梁启超这一观点。在他看来,宋明理学的传统在清代并没有中断。不仅没有中断,而且对清代汉学仍然有甚深的影响。钱穆认为,清代学术由晚明诸老开出,而晚明诸老莫不寝馈于宋学。此后的李塨、方苞、李绂、全祖望等人也都对宋学有很深的造诣。即便是到了汉学鼎盛的乾嘉时代,汉学诸家的高下深浅,也往往“视其所得于宋学之高下浅深以为判”。所以,钱穆提出了清代汉学渊源于宋学,“不知宋学,亦不能知汉学,更无以评汉宋之是非”的见解。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引论”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治近代学术者当何自始?曰:必始于宋。何以为始于宋?曰:近世揭橥汉学之名以与宋学敌,不知宋学,则无以评汉宋之是非。且言汉学渊源者,必溯诸晚明诸遗老。然其时如夏峰、梨洲、二曲、船山、桴亭、亭林、蒿庵、习斋,一世魁儒耆硕,靡不寝馈于宋学。继此而降,如恕谷、望溪、穆堂、谢山乃至慎修诸人,皆于宋学有甚深契诣。而于时已及乾嘉。汉学之名,始稍稍起。而汉学诸家之高下浅深,亦往往视其所得于宋学之高下浅深以为判。道咸以下,则汉宋兼采之说渐盛,抑且多尊宋贬汉,对乾嘉为平反者。故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也。
梁启超把宋学、汉学对为两橛,主要是从反宋学着眼去谈清代学术的,旨在强调清代学术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创新意义。从清代学术本身而言,梁氏的“反动说”无疑有他的合理性。因为清代学术的主流为经学考据,重实证,以求是为宗,与晚明空疏的学风确有不同。从清初开始,学风由虚转实,由主观的推想变为客观的考察,这的确是对宋明之学的一种反拔 。钱穆清学渊源于宋学,“不识宋学,则亦不能知汉学,更无以评汉宋之是非”的主张,主要是从宋明理学的角度来谈清代学术,重在强调宋明学术在清代的延续性和清代学风对宋明的继承性 。就学术思想发展演变的一般过程言,钱穆的“继承说”较梁启超的“反动说”似争更为合理一些。因为:
首先,梁启超把清代学术史仅仅归结为一经学考证史,并非全面。清代学术的主流毫无疑问是经学考证,但这却不足以概括整个清代近三百年间的学术发展史。有清一代,不仅有盛极一时的汉学,与汉学相伴的还一直存在着追寻义理的宋学。即使是在汉学如日中天的乾嘉时代,这种学风依然存在并始终与考据学相颉顽。与考据学大师戴震同时的章学诚揭橥史学经世的旗帜,发出了搜罗遗逸,擘绩补苴、不足以言学的呼声,便是对为考据而考据的乾嘉学风的抗议。而此时讲求经世致用,追求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已在其内部酝酿发皇。到了晚清,伴随着对乾嘉考据学风的反动,有常州公羊学派的崛起。到近代,康有为等人把该派的观点发挥到极致,借经学谈政治,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这些学术思潮,的确是无法用考据学来取代的。钱穆早年就反对把有清一代的学术思想笼统地概括为考证学。他在早年著作《国学概论》第九章“清代考据学”中开篇就说:“言清代学术者,率盛夸其经学考据,固也。然此在乾嘉以下则然耳。若夫清初诸儒,虽已启考证之渐,其学术中心,固不在是,不得以经学考证限也。”到道咸之时,乾嘉汉学流弊重重,乾嘉诸儒的古训、古礼之研究,“其终将路穷而思变”。于是“继吴、皖而起者,有公羊今文之学”。到了清季,康有为“以今文《公羊》之说,倡导维新变法,天下靡然从风,而乾、嘉朴学自此绝矣。”
其次,大凡一种学术思潮的兴起,在前一个时代中可以找到他先存之迹象,同时也不可能在后一个时代中消失得无影无踪。钱穆在《清儒学案·序》中指出:“抑学术之事,每转而益进,途穷而必变。”所谓“每转而益进”,指的是学术思想的继承。前后时代的学术思想无论有多么大的差别,但其中必然有内在的联系,必然有前后延续的成份。而“途穷必变”,则是指学术思想、方法的变革和创新。研究一个时代的学术思想,只看到前后时代的学术差别而看不到继承,或仅着眼于前后的继承而看不到前后时代学术的区别,都是失之片面的,正确的方法应是把二者结合起来进行多方位的全面考察。钱穆研究清代学术史,研究整个中国学术史、思想史,都隐含了这样一种方法。他说两汉经学,并不是蔑弃先秦诸子百家之说而别创所谓经学,而是包孕先秦百家而始为经学之新生。宋明理学,并不是蔑弃汉唐而另创一种新说,而是包孕两汉隋唐之经学和魏晋以来流布中土之佛学而再生。清代学术也不例外。对清初诸儒而言,宋明理学是他们必不可少的知识资源,宋学对他们的影响自不待言。乾嘉诸老以考据为宗,但是他们从事考据的终极目的仍是“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寻义理”,宋明以来相传八百年的理学道统,其精光浩气,仍不可掩。而道咸以来,随着训诂考据一途走向绝境,学者把眼光再次投注宋明理学,汉宋调和、尊宋抑汉风靡学界,经世意识和宋学精神得到高扬,理学重新得以复兴。所以钱穆认为,从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这三百年学术史的大流,论其精神,仍自沿续宋明理学一派而来。诚如所言:“今自乾嘉上溯康雍,以及明末诸遗老,自诸遗老上溯东林以及阳明,更自阳明上溯朱、陆以及北宋之诸儒,求其学术之迁变而考合之于世事,则承先启后,如绳秩然,自有条贯”。 钱穆治学术史,善于把学术思潮的发展变迁置放到思想史本身的运动中加以分析,善于从中国自身的知识和思想资源中去寻找思想史发展的内在理路。他的这一观点和研究方法,在近现代学术界并不是没有赞同者、响应者。比如冯友兰先生在20世纪30年前半期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一书中曾专辟“清代道学之继续”一章来讨论清代汉学与宋明理学的关系,认为清代汉学家表面上虽然表现为反道学,但他们所讨论和关注的问题,实际上仍是宋明道学的继续,与钱穆持有相同的见解 。
三
关于清代学术史的分期,钱穆在《前期清儒思想之新天地》中,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着眼,把清代学术史分为前后二个时期。从顺治入关到乾嘉时代为前期,清初诸儒承袭了宋明儒思想的积极治学传统,在清初学术史上开拓了一片新天地。但到了乾嘉时期,学者在清廷刀锯鼎镬的淫威下走上了训诂考据之路,毕生在丛碎故纸堆里,追求安身立命之所。从道咸起至清廷覆灭为后期,在后期八十年中,一方面是清朝政治腐败,另一方面则是西学东渐,二者给晚清学术思想以极大的影响。在《清儒学案序》中,钱穆从理学的角度出发,把清代学术史分为晚明诸遗老、顺康雍、乾嘉、道咸同光四个阶段,并对四个阶段不同的学术特征作了归纳概括。钱穆的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除第一章“引论”论述清代学术的源起及其与宋明学术的关系外,其余十三章皆以各个时期学术发展史上的代表人物为题。各章所选择的代表人物主要集中在明末清初、乾嘉、晚清三个时期,涵盖了有清一代学术发展史上的经世思潮、经学考据和今文经学等各个层面。这里我们以钱穆先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为考察中心,对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这三百年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作一些论述和分析。
1、清初诸儒之学
在清代近三百年的学术发展历程中,钱穆先生特别推崇清初诸儒之学。他在1928年发表的《述清初诸儒之学》一文中称清初诸儒,“上承宋明理学之绪,下启乾嘉朴学之端。有理学家之躬行实践,而无其空疏;有朴学家之博文广览,而无其琐碎。宋明儒专重为人之道,而乾嘉诸儒则只讲读书之法。道德、经济、学问兼而有之,惟清初诸儒而已。”与此文大约刊出的同时,钱穆在1928年春完成的《国学概论》第九章中,也扼要地勾画出了明末清初群儒的思想。他说“推极吾心以言博学者,有黄梨洲”;“辨体用,辨理气,而求致之于实功实事者,有陈乾初”;“不偏立宗主,左右采获以为调和者,有孙夏峰、李二曲、陆桴亭”;“绝口不言心性,而标‘知耻博文’为学的者,有顾亭林”;“黜阳明而复之横渠、程、朱,尊事物德行之实,以纠心知觉念之虚妄者,有王船山”;“并宋明六百年理学而彻底反对之者,有颜习斋”。 在钱穆看来,在清初诸儒中最有建树的,当推黄梨洲(宗羲)、顾亭林(炎武)、王船山(夫之)、颜习斋(元)四家,所以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5章著重对这四家的学术思想及其清学史中的影响作了专门的研究和阐发。
黄梨洲从学于刘蕺山(宗周),以发挥其师慎独遗教为主。他把读书与求心,博学与良知统一起来,对于矫正晚明王学未流空疏偏狭之弊,极有意义。顾亭林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相标榜,治学明流变,求佐证,不言心性,为乾嘉考据学开一新途辙。但亭林治学以考据为手段,而非目的,其治学宗旨在于明道救世。王船山学宗横渠(张载),“能辟佛老以返诸儒”,论学始终不脱人文演化之观点,其学博大精深,三百年来思想之深刻无出其右。颜习斋论学深斥纸墨诵读之业,对宋明六百年来之理学,高言排出,一壁推倒,“开二千年不能开之口,开二千年不敢不之笔”,在清初学术史上别开生面,独树一帜。
在清初四大家中,顾炎武“经学即理学”的主张对乾嘉考据学风影响至大,乾嘉时期的经学考据实由此而衍生。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顾炎武推崇有加,尊之为清代“汉学开山”。他说顾氏在清代学术界占有最重要的位置,其一在于开学风,排斥理气性命之玄谈,专从客观方面研察事物条理。其二在于开治学方法,如勤搜资料,综合研究,参验耳目闻见以求实证,力戒雷同剿说,虚心改订不护前失等。其三在于开学术门类,如参证经训史迹,讲求音韵,说述地理,研究金石等。故亭林之学,气象规模宏大,乾嘉诸老,无人能出其右。清代许多学术,都由他发其端,后人衍其绪,影响了整个清代学术的去向。 所以梁启超指出,亭林之学“对于晚明学风,表现出堂堂正正的革命态度,影响于此后二百年思想界者极大。所以论清代汉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人”。
钱穆并不否认顾炎武对乾嘉考据学风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并不否认顾炎武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崇高地位。他说亭林“治学所采之方法,尤足为后人开无穷之门径。故并世学者如梨洲,如船山,如夏峰,如习斋,如蒿庵,声气光烈,皆不足相肩并。……其意气魄力,自足以领袖一代之风尚矣。” 但与梁启超所不同的是,钱穆对顾炎武“经学即理学”的思想渊源作了一番穷源竟委的考证和解释,认为此说并非顾氏自创,清初钱谦益已开其先,而钱氏之说又源自明代的归有光。他说:“亭林治经学,所谓明流变,求佐证,以开后世之途辙者,明人已导其先路。而亭林所以尊经之论,谓经学即理学,舍经学无理学可言,求以易前人之徽帜者,亦非亭林独创。考证博雅之学之所由日盛,其事亦多端,惟亭林以峻绝之姿,为斩截之论,即谓经学即理学,因以明经即明道,而谓救世之道在是” ,故其说遂为后世瞩目。
在钱穆看来,对乾嘉考据学风影响很大的并非顾炎武一人,在晚明诸遗老中,黄宗羲的影响就不小。此说在他早年著作《国学概论》中已有阐发,在《近三百年学术史》“梨洲经史之说”中亦详加讨论。黄氏考证《易经》,著《易学象数论》六卷,力辨河、洛方位图说之非,而遍及诸家。胡渭著《易图明辨》,卷末备引其说。著《授书随笔》一卷,实开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之先导。又究天文历算之学,亦开风气之先,著《授时历故》等书,俱在梅文鼎前。于史学,贡献特大,为浙东史学的开创者。浙东史学自梨洲开其端,一传为万季野(斯同),再传为全谢山(祖望),止于章实斋(学诚),遂与吴、皖汉学家以考证治古史者双峰并峙,交相辉映。钱穆认为,黄宗羲为矫晚明王学空疏之弊,力主穷经以为根底,已为新时代学风开一新局,其影响后学,实不在顾亭林之下。后人言清代汉学,不提黄氏的影响,全以顾亭林“经学即理学”为截断众流,是因为顾氏之说符合汉学家的口味,而梨洲则以经史证性命,多言义理,不尽于考证一途,故不为汉学家所推重。钱穆认为,清代学术在乾嘉时期走入顾氏“经学即理学”一途,浙东精神未能彰显于世,这实在是清代学术史上一件值得令人惋惜的事 。所以他批评梁启超把清代汉学开山归于顾氏一人之力,为“失真之论” 。
2、乾嘉经学考据
清代学术发展到乾嘉时代,抛弃了顾炎武、黄宗羲等晚明诸儒通经致用的思想,演变成为考据而考据,为学问而学问的学风。所以,清初经世致用的学术精神至乾嘉考据学风的兴起而大变,其学术精神在考据而不在义理。乾嘉考据之学至吴人惠栋、皖人戴震已臻全盛,尊汉排宋,风靡学界。所以钱穆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6—10章专论乾嘉考据之学。
将乾嘉考据学分为吴、皖两派,在江藩《汉学师承记》中已露端倪,而将两派学术异同作区分并加以论述的则首起于章太炎。他称清儒“其成学著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江永、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异也。” 梁启超继承章氏之说而发以发挥,认为吴派为学淹博,拘守家法,专宗汉说;皖派治学不仅淹博,且重“识断”、“精审”。于是惠、戴之学中分乾嘉学派,遂成定论。吴、皖两派分帜对立之说创立以来,学术界多遵章、梁之说,不免忽略了两派之间的学术联系。钱穆在研究乾嘉学术时,不仅看到了吴、皖两派的学术区别,更重要的是看到了两派之间的学术联系及其相互影响,这体现了他治学的敏锐和识见精深之处。钱穆认为,苏州惠学尊古宗汉,意在反宋,惠栋即有“宋儒之祸,甚于秦灰”之说。而皖南戴学却“从尊宋述宋起脚”,初期志在阐朱述朱,与反宋复古的吴学宗旨不同。但自乾隆22年(1757年),戴东原(震)北游后南归,在扬州见到惠定宇(栋)以后,其学大变,一反过去尊宋述朱转而诋朱排宋,而戴门后学,排诋宋儒,蔚为风尚,乾嘉汉学由是大盛。钱穆认为,“乾嘉以往诋宋之风,自东原起而愈甚,而东原论学之尊汉抑宋,则实有闻于苏州惠氏之风而起也”。 他在《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列出了多条理由以证其说 ,得出了“东原极推惠,而惠学者亦尊戴,吴、皖非分帜”的结论。所以,钱著以惠、戴论学有舍,交相推重为由,将二人同列一章,即体现了这种布局安排。
由于钱穆力主清学导源于宋学,重视宋明理学对清代学术的影响,所以其著作在内容的安排上,特别注重发掘清儒对宋明理学问题的探讨,即便是在汉学全盛的乾嘉时代,书中的编纂布局亦是如此。钱著笫八章以戴东原为题,而以江慎修(永)、惠定宇(栋)、程瑶田(易畴)附之。江、戴、程三人皆歙人,以江、程附戴,目的在于厘清戴学的学术渊源。钱穆指出,徽、歙之间,乃朱子故里,学者讲学,多尊朱子,故尚朱述朱之风,数世不辍。对于皖学的渊源,钱穆在《国学概论》中作了这样的叙述:“徽州之学,成于江永、戴震。江(永)治学自礼入。其先徽、歙之间,多讲紫阳(朱子)之学,远与梁溪、东林相通,(江)永盖承其绪风,东原出而徽学遂大,一时学者多以治礼见称。”在《近三百年学术史》中,钱氏作了更详尽的考证:“考徽、歙间讲学渊源,远自无锡之东林。有汪知默、陈二典、胡渊、汪佑、吴慎、朱璜讲朱子之学于紫阳书院,又因汪学圣以问学于东林之高世泰,实为徽州朱学正流,江永、汪绂皆汲其余波。故江浙之间学者多从姚江出,而皖南则一遵旧统,以述朱为正。惟汪尚义解,其后少传人,江尚考核,而其学遂大。” 江氏之学传至东原,形成皖学。钱穆述东原之学源于徽歙,戴学源出朱子,其用意主要落在宋学对戴氏的影响上。这说明皖学自绍宋入手,与吴学自攻宋起脚异趣。戴氏晚年排诋宋儒,刻深有过颜李,所以章学诚力斥东原攻朱子之非,讥其“饮水忘源”。钱著第十章以焦里堂(循)、阮云苔(元)、凌次仲(廷堪)为题而附之以许周生(宗彦)、方植之(东树),也体现了这种安排。焦循、阮元、凌廷堪学尊东原,为考据名家,但钱穆看重的并不是他们在考据学上的成就,而是把眼光投注到他们对汉学流弊的反思和批评上。钱穆指出,焦氏之学“主用思以求通”,与当时名物训诂逐字逐句的零碎考释学风已有不同。阮元“颇主求义理,故渐成汉宋兼采之风。”而凌廷堪对当时汉学流弊多有不满,有“不通世务,不切时用”,“好骂宋儒,而高自标置”,“意气日盛”等批评之语 ,实开近代抨击乾嘉学风之先声。焦、阮、凌三人皆为汉学考据大家,却群起批评自己学派的短弊,从中亦可透显出一个学术转变的新时期即将来临。故此章以考据学风的批评者许宗彦附于三人之后,又以攻击乾嘉汉学最烈的方东树殿尾,无非是要向人们表露这样一个信息:乾嘉汉学此时流弊重重,逐渐失去了学术界的支持,“路穷而思变”,此后的学术路向必然要向汉宋兼采的方向发展。此章的谋篇布局,可谓匠心独运 。
3、常州今文学派
在考据学风弥漫的乾嘉之际,公开站出来批评这种学风、树反汉学旗帜的有史学家章学诚。章氏祭起“学术当以经世”的旗帜,高唱“六经皆史”之说,对乾嘉汉学埋首考据的琐碎学风大加抨击。到道、咸之际,随着训诂考证一途走向绝境,有追求微言大义的常州今文学派的异军突起,湮灭了一千多年的西汉今文经学重新得以复兴。钱穆指出,常州今文学派“起于庄氏(存与),立于刘(逢禄)、宋(翔凤),而变于龚(自珍)、魏(源)。”所以钱穆《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1章以龚定庵(自珍)为题,附之以庄方耕(存与)、庄葆琛(述祖)、刘申受(逢禄)、宋于庭(翔凤)、魏默深(源)、戴子高(望)、沈子敦(垚)、潘四农(德舆),对晚清最重要的学术思潮常洲今文经学作了专门论述。
常州之学由庄存与开其端,庄氏不专为汉宋笺注之学,著《春秋正辞》,旨在阐发《春秋》的微言大义。常州公羊学至庄存与的外甥刘逢禄、宋翔凤时张大旗帜。常州言学,主微言大义,而通于天道人事,最终必归趋于论政,开此风气之先者首推龚自珍。龚氏一反当时经学家媚古之习,而留情于当代之治教,于是盱衡世局,而首唱变法之论。魏源继之,以“经术为治术”,欲“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至康有为时,以经学谈政治,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于是常州之学,终于掩胁晚清百年来之风气而蔚为大观。钱穆认为,常州今文学之初期,专言公羊,不及他经,至龚、魏时而大变,由信公羊转而信今文,轻古经而重时政,而龚、魏之主张实承章学诚而来。在钱穆看来,乾嘉汉学揭橥为学问而学问的旗帜,为学重在实事求是,而常州今文学派重在舍名物训诂而追求微言大义,这已失去了汉学精神,乾嘉考据之学至此声光不存。
清代今文经学极于康有为,所以钱穆对清代学术史的研究终于康氏。晚清的今文经学至龚、魏而蔚为大观,到廖平、康有为时集其大成。特别是康有为继承常州今文学派的观点大加发挥,其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为现实的政治需要随意解释六经,取舍、改铸历史,其弊以至“颠到史实而不顾”。钱穆称“康、廖之治经,皆先立一见,然后搅扰群书以就我,不啻‘六经皆我注脚’矣,此可谓之考证学中之陆王。而考证遂陷绝境,不得不坠地而尽矣。” 在钱穆眼中,晚清今文学家走的是“一条夹缝中之死路,既非乾嘉学派所理想,亦非浙东史学派之意见。考据义理,两俱无当。心性身世,内外落空。既不能说是实事求是,亦不能说是经世致用。清儒到道咸以下,学术走入歧道,早无前程”。 学术之事,“每转而益进,途穷而必变”,此下的学术路径必然有变,不能再循此三百年的老路走下去了。
四
钱穆治清代学术史主要以昂扬宋学精神为主旨,所以他在评价和判识清代学人学术思想的高下浅深时,就贯穿了一条是否有志经世、是否心系天下安危的宋学精神为其评判标准的。钱穆屡屡道及的宋学、宋学精神,实际上就是宋明儒提倡的学贵经世明道,讲求义理,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精神。
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引论”中,对清代学术的直接源头给予了具体解析,认为清学直接来源于晚明的东林学派。钱氏对东林学派之所以情有所钟,就是因为东林学者是真正有志经世、坚守气节、重在实行的学者。东林讲学大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矫挽晚明王学末流空谈心性之弊,一是抨弹政治之现状。他们对王学末流的批判开启了清儒辨宋明理学的先河,而对当时政治的批评对清初诸儒的议政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东林学人坚持于牢狱刀绳下的民族气节和崇高的人格更是为清初诸儒所激赏。所以,东林学者的气节操行和避虚归实、重在实行的精神直接影响了清初诸儒。
钱穆对清初诸儒评价甚高,认为清初诸儒之学胜于乾嘉经学考证,就是清初诸儒论学犹有宋学经世明道的精神。钱穆在《述清初诸儒之学》中称:“道德、经济、学问兼而有,惟清初诸儒而已”。这里的所谓“经济”,即经国济世之学问。清初诸儒不仅笃学博文,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将其学问措之世用,与王学末流空谈心性、束书不观和乾嘉学者不问世事、皓首穷经截然异趣。比如黄宗羲为王学蕺山一派传人,但其论学,重实践,重工夫,重实行,“既不蹈悬空探索本体,坠入渺茫之弊”,“又不致陷入猖狂一路,专任自然”。船山论学,“所长不仅在于显真明体,而尤在其理惑与辨用焉”,所论政治、社会、人生种种问题,“皆能切中流俗病痛,有豁蒙披昧之功”。顾亭林以知耻博文相标榜,其论学宗旨在于明道、救世。吕晚村(留良)阐扬朱子,其意在于“发挥民族精神以不屈膝仕外姓为主”,实非康雍以下诸儒仰窥朝廷意旨,以尊朱辟王为梯荣快捷方式者所能相比。而颜习斋论学之真精神在于,“不从心性义理分辨孔孟程朱,而从实事实行为之分辨”,力倡章句诵读不足以为学,所常道者为兵、农、六艺、礼乐等有用之学。清初诸儒生活在国家颠覆,中原陆沉,创巨痛深,莫可告语的时代环境中,他们行己持躬,刻苦卓励,坚贞不拔的气概和厉实行、济实用的学问,“足为百世所仰慕”。钱穆对清初诸儒这种不忘种姓,有志经世的精神和坚守民族气节称赞不已,因为从他们身上体现了宋明儒经世明道,以天下兴衰安危为己任的真精神。对此他情不由己地赞道:“每读史至此六七君子者,而使人低徊向往于不能已”。
清初学术至乾嘉而大变,学者埋首书斋,专事考据,皓首穷经。这种优游于太平禄食之境与清初诸儒不忘种姓,有志经世的精神意气异趣。对此钱穆颇有感触的说道:“清初诸老讲学,尚拳拳不忘种姓之别,兴亡之痛,家国之治乱,身世之进退。而乾嘉以往,则学者惟自限其心思于文字考订之间,外此有弗敢问。学术思想之转变,亦复迁移默运,使屈膝奴颜于异族淫威之下而不自知,是尤可悲而可畏之甚者也。” 在钱氏看来,乾嘉诸老忘记了顾亭林等清初诸儒的“行己”之教,而专师其“博文”之训,为学问而学问,已失去了宋明儒学贵经世明道,以天不为己任的真精神 。所以,他对这种逃避人生,喜为零碎考释的学风大加抨击,批评乾嘉学者不通学问大体,称“学问之事,不尽于训诂考释,则所谓汉学方法者,亦惟治学之一端,不足以竟学问之全体” 。“治学而专务为琐屑之考据,无当于身心世故,则极其归必趋于争名而嗜利,而考据之风,亦且不可久”。“乾嘉之盛斥宋明,而宋明未必非” 。象这样的批评之语,屡见于他治清代学术史的论著中,这与梁启超对乾嘉朴学的治学方法大加赞扬,誉为“科学的古典学派”的评价大不相同。
钱穆在评价清代学术史时,以表彰宋学,批评汉学流弊为己任,这与他对当时学术界盛行的考据学风的反思和批判有关。20世纪20年代,在胡适“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口号声中,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汉学运动。以傅斯年为首,以史语所为阵地、以整理和考辨史料为鹄的的“新考据派”,(或称“史料考订派”、“史料学派”)便是这场新汉学运动的产物。该派对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影响深远,成为当时史坛上的“主流派”。钱穆早年以考据名家,他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均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考据名作,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不失为新考据派的同志。事实上,新考据派对钱穆在考据学上的成就也是承认、称道的。三十年代初,钱穆之所以能入北大史学系任教,除了古史辨派的主将顾颉刚的力荐外,还与史料考订派的舵手傅斯年的有意相邀、新汉学运动的领袖胡适的接纳有关 。而钱穆对新考据派重建古史的工作也寄予厚望,有“确然示人以新观念、新路向”的积极评价。钱穆虽然以考据名家,他早年治史深受乾嘉考据方法的影响,但他却并不赞许乾嘉史学 。因为他认为“考据之终极,仍当以义理为归宿”,不能单凭考据便认为尽了学术研究之能事,更不能沉溺于烦琐考据而忘掉了学术经世的宗旨。他说乾嘉经学考据之大病,“正在持门户之见过深,过分排斥宋儒,读书专重训诂考据,而忽略了义理。” 而五四以来的新考据派则把乾嘉汉学为考据而考据的学风发挥到极至。在钱穆看来,新考据派最初本求摆脱乾嘉而转向西方输入学理,当他们步趋欧美,引进西方实证主义史学方法后,才发觉“欧美与乾嘉,精神蹊近,何其相似,乃重新落入乾嘉牢笼”,言学仍守故纸丛碎为博实。新考据派推崇乾嘉治学方法,专走训诂考据之路,这是深受宋明学术思想影响的钱穆所不能赞同的,这就引发了他对该派学风的批判。他称新考据派专事考据,毕生在故纸堆里驰骋心力是“不得大体,而流于琐碎”,“于身无益,于世无补。”对近人认定的宋学为疏陋之学,“至清始务笃实”的观点,他也大加批驳,称“自宋以下学术,一变南北朝隋唐之态度,都带有一种严正的淑世主义”,“以天下为己任,此乃宋明以来学者惟一精神所寄。” 事实上,自30年代以来,学术界不少学者对新考据派烦琐的考据学风提出了批评,1934年张孟劬在给夏承焘的信中说:“今日考据之弊,甚于空疏,且使人之精神,日益逡外,无保聚收敛以为之基,循此以往,将有天才绝孕之患。” 而另一部分不失传统士人精神的学者,则祭起学术经世的旗帜欲以救世,宋明学术精神再一次得到高扬,钱穆先生可谓是这一部分学者的代表。与钱氏声气相通、引为同调者在当时还有陈寅恪、冯友兰等学者。陈寅恪曾说:“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熏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 而冯友兰则明确指出他撰写《中国哲学史》的宗旨就在于昂扬宋儒“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大平”的精神。
钱穆推崇宋儒,表彰宋儒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这还与当时受国难的刺激有关。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写于“九一八事变”之后,当时日本侵占东三省大好河山,步步进逼华北。1935年,日军策动“华北自治”,诺大的华北五省,“已经不能安放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当时在北平任教的钱穆,目睹日寇猖獗,痛心疾首,“斯编初讲,正值九·—八事变骤起。五载以来,身处故都,不啻边塞,大难目击,别有会心。” 冯友兰先生在当时也发出了与钱穆同样沉重、激愤的呼声。他在《中国哲学史》自序(二)中说:“此第二篇稿最后校改时,故都正在危急之中。身处其境,乃真知古人铜驼荆棘之语之悲也。值此存亡绝继之交,吾人重思吾先哲之思想,其感觉当如人疾痛之见父母也。吾先哲之思想,有不必无错误者,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乃吾一切先哲著书立说之宗旨。无论其派别为何,而其言之字里行间,皆有此精神之弥漫,则善读者可觉而知也。”钱穆出生在甲午战败、台湾割让日本之年,他的一生与中国甲午战败以来的时代忧患相终始,一生的著述讲演无不是“在不断的国难之鼓励与指导下困心衡虑而得”,无不从“对国家民族之一腔热忱中来”。面对日寇的步步侵逼,具有强烈民族忧患意识和强烈民族情感的钱穆愤慨尤深,在撰述中自然会有所流露。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特严夷夏之防,高扬以天下为己任的宋学精神,表彰清初诸儒不忘种姓的民族气节和操行,即寓有他反抗外来侵略的写作意图。杨树达先生在读钱著时就有“注重实钱,严夷夏之防,所见甚正”的评价 。而三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尚崇乾嘉考据之学,“薄致用而重求是”,“言学则仍守故纸丛碎为博实”,贬抑宋学,“持论稍近宋、明,则侧目却步,指为非类”。在钱穆看来,这种学风尤其有害,特别是在日寇步步进逼,侵夺我大好山河之时,这种不问世事,埋首书斋的考据学风不利于鼓劢民众团结起来,抵抗侵略 。所谓“大难目击,别有会心”,就是要弘扬近三百年来所晦沉、为时代所讥刺的宋学精神来救世济民。所以,弘扬学贵经世,以天下兴亡为念的宋学精神,成为了钱穆治清代学术史的意旨所在。
钱穆治清代学术史,发清学导源于宋学之见,对清代学者的学术渊源、师承及其思想抉发精微,不少见解很有价值。但是,钱氏的观点也并非没有可商榷之处。比如他对晚清今文经学,特别是对康有为思想的评价。晚清今文学派批评乾嘉汉学,揭橥为学贵在经世致用,这与钱穆批评汉学流弊,高扬宋学精神的旨意相同。照理说,钱穆对晚清今文思潮应有较高的评价,然而事实却恰好相反。钱穆说道咸之际兴起的常州之学,“其实则清代汉学之旁衍歧趋,不足为达道。而考据既陷绝境,一时无大智承其弊而导之变,彷徨回惑之际,乃凑而偶泊焉。其始则为《公羊》,又转而为今文,而常州之学,乃足以掩胁晚清百年来之风气而震荡摇撼之。卒之学术治道,同趋澌灭,无救厄运,则由乎其先之非有深心巨眼、宏旨大端以导夫先路,而特任其自为波激风靡以极乎其所自至故也。” 又说:“晚清今文一派,大抵菲薄考据,而仍以考据成业。然心已粗,气已浮,犹不如一心尊尚考据者所得犹较踏实。其先特为考据之反动,其终汇于考据之颓流。” 钱穆称晚清今文经学为清代汉学考据的“旁衍歧趋”,今文学者“大抵菲薄考据仍以考据成业”,这从事实的层面讲,大体是不错的。因为晚清今文学者的治学方法的确是沿考据一路而来,即便是今学经学的集大成者康有为,他撰《新学伪经考》也是在披着考据的外衣下进行的。但是有一点尤需明白,在晚清今文学者眼中,考据是手段,是形式,而不是目的,他们是通过考据这种形式为其政治目的张目,即以考证之名,而行学术干政之实,其着眼点在政治而非学术一边。易言之,是真用结合,还是弃真求用,晚清今文学派显然选择了后者。钱穆本是主张真用结合的学者,但在评价晚清今文思潮时,他却仅站在“求真”的立场上加以审视批评,似乎又退到了以古文攻今文的立场,不免忽略了晚清今文思潮崛起的时代背景及其他们在社会政治层面的贡献。这一点,在评说康有为的思想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康氏的《新学伪经考》称古文经尽出刘歆伪造,目的是要为新莽王朝代汉制造舆论。钱穆从学术求真的层面上对其说绳之以学理,称康说多主观武断处,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是,仅从学术层面上去批评康说,并不全面。因为康氏之书是在借经学谈政治,目的在于为维新变法鸣锣开道,其价值主要在政治而非学术—边。钱穆在这方面似乎甚少注意,时人对钱氏评价康说就有“特见其表面,未见其精神” 的批评。又如,清人崔东壁(述)的疑古辨伪,直接开启了近代的疑古思潮,对“五四”以后的学术界影响深远,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就是承此风而起的。然而钱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竟不列崔述,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注释:
1.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617页。
2.《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2册,第639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
3.陈祖武:《清代学术拾零》,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0页。
4.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反动与先驱”一节中从五个方面列举了明末清初以来的反理学思潮,最后得出结论:“后来清朝各方面的学术,都从此中(即对宋明理学的反动–引者)孕育而来。”参见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7~102页。(以下所引梁着《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皆据此书)与梁启超同声相应的还有胡适,他在《戴东原的哲学》“引论”中说:“中国近世哲学的遗风,起于北宋,盛于南宋,中兴于明朝的中叶,到了清朝,忽然消歇了。清朝初年,虽然紧接晚明,已截然成了一个新的时代了。自顾炎武以下,凡是第一流的人才,都趋向到做学问的一条路上去了,哲学的门庭,大有冷落的景况。”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39页。
5.周国栋认为,余英时把梁启超的“反动说”视为外缘说的观点不甚合理,就清学本身而言,“反动说”似乎更为合理,他列出了四条理由。参见氏著:《两种不同的学术史范式─—梁启超、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比较》,《史学月刊》2000年第4期。
6.朱维铮认为,钱穆主要从宋学着眼谈清代学术,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实际上写成的是清代“宋学”史,其书的学术价值也因此而彰显。参见氏著:《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题记”第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7.钱穆新亚时期的学生余英时力主师说,在《从宋明儒学的发展论清代学术思想》、《清代学术思想的一个新解释》等文中对乃师的观点多有论述、发挥,可参阅。
8.参见钱穆:《国学概论》,第310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
9.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页,以下所引此书皆据此版。
10.冯友兰认为,宋明人所讲的理学与心学,在清代皆有继续的传述者。清代汉学家讲义理之学,其所讨论的问题,如理、气、性、命等,仍是宋明道学家所提出的问题;他们所依据的经典,如《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仍是宋明道学家所提出的四书。所以,清代汉学家所讲义理之学,表面上虽为反道学,而实则系一部分道学之继续发展。参见冯氏《中国哲学史》第十五章“清代道学之继续”中“汉学与宋学”一节的论述。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74页—975页。
11.参见钱穆:《国学概论》,第246页—253页。
12.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见朱维铮《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163页。
13.同上,第153页。
14.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46页。
15.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41页。
16.在钱穆看来,对乾嘉考据学的影响,顾、黄二人贡献尤大,若谈清代汉学开山,应以顾、黄二人并举。关于此点,清人江藩已有注意。可参见《汉学师承记》卷8附跋。
17.根据钱穆的考证,顾炎武研究古音,用“本证”、“旁证”之法源于明代学者陈第的《毛诗古音考》,而梁启超“误以陈氏本证、旁证语为亭林自述,因谓亭林为汉学开山。证据既误,断案自败。”参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36页。
18.《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473页。
19.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22页。
20.钱穆认为乾隆二十二年,戴震与惠栋见于扬州,论学有合,交相推重,以后又客居扬州四年,是其一生为学的重要转变时期。戴震以朱学传统反攻朱子,排诋宋儒,此实受惠栋思想的影响。他到举了这样几条理由:一是乾隆三十年,戴震为纪念惠栋而写的《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文中议论与以前大异,此为“东原论学一转而而近于吴学惠栋之证”。二是乾隆三十四年,东原为惠栋弟子余肖客序《古经解钩沉》,从序中内容可知“东原此数年论学,其深契乎惠氏”。三是东原著《原善》三篇,时间大约在他游扬州识惠栋之后,其文言“理”,颇受惠氏《易微言》的影响。参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22—327页的相关论述。
21.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09—310页。
22.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506—508页。
23.此处叙述采纳了路新生的研究成果,见氏著《梁任公、钱宾四《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合论,台北《孔孟学报》第68期。
24.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笫652页。
25.钱穆《前期清儒思想之新天地》,《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0年,第11页。
26.钱穆:《述清初诸儒之学》,《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2册,第4页。
27.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72页。
28.钱穆称亭林论学宗旨在于“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二语上,但是亭林后学仅师其“博文”之训,忘其“行己”之教,致使其经世明道的真精神不能彰显于世。为此钱穆不无感叹地说:“三百年来,亭林终不免以多闻博学见推,是果为亭林之辱欤!亭林地下有知,客死之魂,不知又于何归依。今谓亭林为清学开山,亦仅指其多闻博学,而忘其行己有耻之教者,岂不更可痛之其耶!”参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31页。
29.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402页。
30.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525页。
31.参见拙著:《钱穆传》,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5页。
32.据钱穆晚年回忆,“余本好宋明理学家言,而不喜清代乾嘉诸儒之为学。及余在大学任教,专谈学术,少涉人事,几乎绝无宋明书院精神。人又疑余喜治乾嘉学,则又一无可奈何之事矣。”参见《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45页。
33.钱穆:《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该文作于1935年,见《学蘥》,第82页,香港1958年自印本。
34.《国史大纲》,上海商务编译馆1947年版,第620页。
35.转引自王汎森:《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见罗志田编:《20世纪的中国与学术·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8页。
36.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从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77页。
37.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第4页。
38.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04页。
39.事实上,由于受国难的刺激,一些专事考据的学者也在自我反省,转变学风。如史学家陈垣先生曾说“从前专重考据,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见陈乐素、陈智超编校:《陈垣史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24页。
40.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525页。
41.钱穆:《中国近三百着选》,年学术史》第532页。
42.赵丰田:《读钱著康有为学术述评》,《大公报》2025-08-04。
原载《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1期